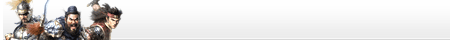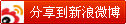没有交际对象的言语交际是不存在也是无意义的。而交际对象影响甚至决定着交际内容和言语表达形式的选择。”因而对交际对象的考察与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三国演义》第十回曹操因父亲全家被张闿所杀,迁怒于陶谦,要屠戮徐州,陈宫以仁义相劝,就是没有把握住说劝对象奸雄曹操的性格特点。无异于隔靴搔痒,自说自话,反而使曹操大不耐烦,说劝没有起到丝毫的效果。第九十六回诸葛亮错用马谡,出师不利,回到西蜀请求自贬后,费祎恐他羞愧以蜀兵取得的小胜出言安慰,反而让诸葛亮“变色”、“怒曰”,也是因为没有把握住交际对象的人格特点和心理状况。诸葛亮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反省自责,以国家大事为重,一心想的是如何避免失误再次伐魏,并没有将个人的荣辱名位放于心中。费祎的话在他听来无异于逢迎拍马而且无益于事,当然倍觉刺耳而不愿再听。
我们知道要想使交际对象接受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就必须能够改变交际对象的固有态度。而态度是根据经验而构成的一种心理或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对有关事物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动力性的影响。”也就是“个人对某对象所持有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成功的言语交际者,总是能够善于使交际对象的态度转换成自己需要的另一种态度。现代心理学认为态度包括认识、情感和意向三种成分,而“情感因素在态度诸要素中是较为稳定的心理成份”、“情感常常决定着意向”。所以改变交际对象的态度,则以改变交际对象敌对或对立的情感为最便捷和有效的途径。《三国演义》中张辽能够成功地说服关羽屈身曹营,就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例证。张辽深知关羽只可理说之,不可势屈之,因而单骑跑马上山,声称以“故人旧日之情,特来相见”,就首先缓和了双方敌对的情绪。接着他紧紧扣住关羽信奉忠义,以忠义标榜的性格特点和誓死以全忠义的心理意识,振振有辞地提出“三罪”说,认为关羽若一心求死则正是不忠不义,一下子封住了关羽的退路和说辞,使关羽沉吟踌躇,情感上不再认为张辽是令人厌憎的说客而觉得他是避免自己陷入不忠不义困境的朋友,心理上顿时拉近了距离,求死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最终寻求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解决途径。
任何言语交际都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下进行的,交际环境同样能够深刻影响言语交际的成败得失。这种环境既包括大的社会环境,也包括具体的交际情境。三国使者如赵咨、邓芝、宗预等能够游说成功,不仅仅与他们能言善辩、有胆有识有关,也脱离不了三国鼎立既勾心斗角又唇齿相依的大环境。而善于利用具体的言语交际情境,常能获得出奇的效果。较为精彩的是第五十九回的“曹操抹书间韩遂”。曹操为了破坏马超与韩遂的联盟首先故意在阵前与韩遂马头相交,寒温叙旧,回营后又单送韩遂一封涂抹的书信,使马超疑心重重。韩遂只得答应第二天阵前引曹操出来,让马超刺杀。结果曹操让曹洪马上欠身回答:“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切莫有误。”本来只是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并不能真的说明什么,但马超既已疑心于前,又亲耳听到这样的话,顿时认定韩遂通敌背反,勃然大怒,要刺韩遂,曹操的离间获得了成功。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晋·陶渊明)运用现代言语交际学的知识进行理性的审视,我们就可以合理的解释《三国演义》中人物言语交际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交际内容和交际手段并不是仅有的决定因素,成功的言语交际应该是综合运用言语交际诸要素的结果。尽管作为古人的罗贯中,不可能自觉地有意识地用言语交际学的知识来设计与组织,但那些成功的范例却又恰如其分地契合了言语交际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三国演义》中人物成功的言语交际,所折射出的不仅是身处于交际情境中的三国人物智慧的光彩,同时也折射出作者罗贯中杰出智慧的辉光,使他不愧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巨匠,深受后人的景仰。